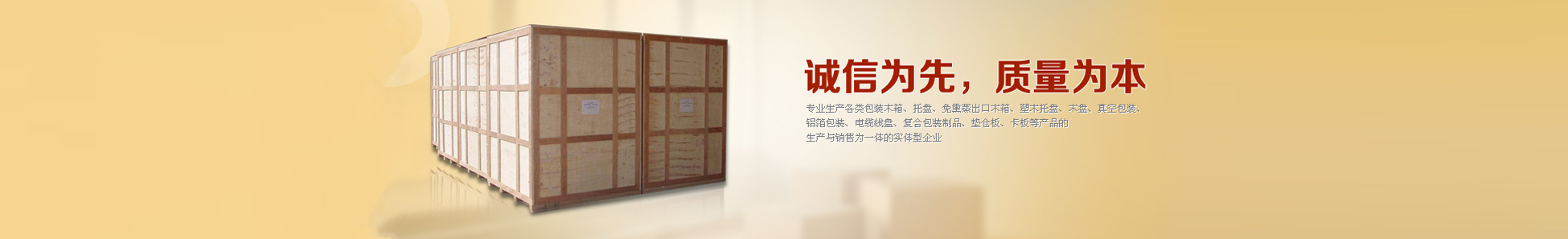身兼母亲与艺术家的身份,蒋雨以平均一年半一次个展的频率高效运转。个展“半梦浮生中的提问”之后,2025年春天她带着个展“褶皱与浮光”在上海亮相。此次展出的30余件新作,延续了她一贯遵循的立足于现实,并以“纯真”原则来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的工作方法,同时也在发生改变。她的每一次改变都与女儿有关。恰如女儿出生后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化,与女儿一同成长的蒋雨的绘画,在女儿进入青春期后步入新阶段。
“比起我带给女儿的快乐,女儿给予我的更多。纵使偶尔也会闹矛盾,但我们仍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”蒋雨对《艺术栗子》说。诚然,随着女儿的出生,此后的每一张画都少不了与女儿的牵绊。
如果说生育是很多女性艺术家跨不过的一道坎,在蒋雨这里则是顺滑且自如。198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她,在家人的呵护中长大。小时候,妈妈知道她想学画画,二话不说就带她报班;外公带她外出写生,外婆给她买画画的本子和颜料;在美院教书的表舅妈,亲自传授她画画的技能。当女儿变成母亲,这个爱的接力棒自然传递到蒋雨手中——女儿成为她的灵感缪斯。
美术史中不乏描绘女儿的经典画作,像蒋雨这样将女儿作为主要母题的并不多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,她既要处理与女儿的琐碎日常,也要随时带有艺术家的观察,捕捉那动人的情绪与微妙的感受。
女儿的到来,让原本作息不规律的蒋雨,有了固定作息表。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成长,她读了很多与儿童心理学相关的书籍。这些看似所有妈妈的日常,最终对艺术家画面中的秩序和内容构成影响,那些有些蒙太奇的处理手法,正是对那一刻内心世界的超现实描绘。
在很多画面中,植物和动物的大小与人成等比例关系,中性面孔、表情淡然的孩童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,周边伴随着一些随时代发展渐渐淡出生活的事物,如弹子球、发条、旋转木马等。精简画面的同时将相关元素放大,在布面上使用丙烯结合油画与工笔技法作画,色彩明媚又不会过于艳丽。这样的创作基调奠定于一次接送女儿的经历。
在孩子的幼儿时期,蒋雨的妈妈经常带外孙女出去玩。夏季傍晚彩霞满天,人烟稀少的车站,盘旋在车站附近的蜻蜓、燕子之类的动物自成“主角”。某天去车站接女儿的蒋雨被这个场景击中,看着跑向自己的女儿,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,此后便有了《乘客》。在这一刻,女儿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在她身上具象化了,也是艺术家身份的她的新生。
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,再到蹒跚学步,直到如今的初长成。女儿每一个阶段的成长,都会带给她不同的生命感悟。透过孩子的眼睛,她重新观察这片广阔的天地,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
在女儿还是幼童时,她发现小孩子总是能专注地观察一只小昆虫、一个小动物,并乐此不疲。但是,成人在日复一日地忙碌中,把四季都错过。那天之后,比起过往,蒋雨更加能留意到身边植物的变化,她会驻足赏花,也会抬头看看飞翔的小鸟。
步入及笄之年的女儿,让她看到了二人之间的共性和特性。青春期的孩子身上会有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隐秘情绪,蒋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私密的状态,并通过“成长纪实”系列与女儿再次一同长大。这也是女性才能拥有的一项“特权”——孕育一个新生命,等于“重启”一次人生。


《成长纪实——此刻》中穿着舞鞋趴睡在书本上的小女孩,正是蒋雨女儿的真实瞬间。不同的是,艺术家将这一场景做了蒙太奇处理,上了发条的孩子要在繁重的课业中,马不停蹄地奔跑。为此,女儿不得不看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书,喜欢的舞蹈也要被搁置。
蒋雨为此感到惋惜,画作上的发条暗喻了社会中的人们仿佛都被装上了枷锁,疲于奔走。发条最终可以停下来,艺术家在这个细节的设定上寄托了美好的期盼,希望人类能时不时停下来、想一想。
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、走过的路,皆能成为蒋雨入画的素材。虽然画中每一个素材都是如此真实,但隐隐透露着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。失衡的动植物、宛如置身梦境的场景塑造、降低纯度的色彩使画作笼罩着怀旧气息……


为数不多的几张关于“剧场”的作品,是蒋雨众多系列中怀旧气息最浓厚的,且带着点点惆怅。一则太阳马戏团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,勾起了她的回忆,也促生了这个系列的诞生。
太阳马戏团是全球久负盛名的马戏团,在蒋雨的孩童时期,也有相似的中国本土大小马戏团巡回演出。她记得长长的大卡车拉来远方的大象、猴子、狗等各式各样的动物和穿着奇异的男男女女。买票进入他们搭建的大型帐篷里看动物表演跳火圈、叠罗汉……以及小丑表演和各类高空杂耍,真叫人眼花缭乱。马戏团是一个既残忍又美好的场域,美好之于人类,残忍之于动物。
蒋雨和女儿共同养育一只猫后,她愈发觉得万物皆有灵,给人春风拂面般的感受。这也是她用动物填补画面空白,并且占据相当比例的另一个原因。
那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元素,在蒋雨的作品中总是格外令人瞩目。比如《乘客》里的公交车、《公园日记——南郊往事》中的踏游船、《玻璃球游戏》里的弹子球……这一些细节都承载着她对儿时记忆的追溯。
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中,蒋雨通过女儿的生活点滴,逐渐唤醒自己童年的回忆。她用绘画的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巧妙地将上代人与当下时代的童年融合在一起,在带有间离感的同时,又为两代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亲切感。
曾经有观者感叹蒋雨的画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,脱离了日常生活经验的范畴。她因此更能直观地体会到,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的加速发展,已经使得不同代际的人们在对生活的认知上产生巨大鸿沟。感到魔幻,只因陌生;认为陌生,只因不了解。这使她更加坚定了在画作中融入剧场元素的想法。


为了增添一丝观展的趣味,《玻璃球游戏》将画作于木盒盖上,盖子打开是满满一盒色彩各异的玻璃球,观众可以随意把玩,并带走。在那个没有电子玩具的年代,小小的玻璃球承载着80后、90后儿时纯粹的欢乐,它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光芒,就像童年那段无忧无虑、闪闪发光的时光,如今轻轻一握,仿佛就能回到逝去的岁月,满是温柔。
不记录就会消失,而消失了的,都会成为纪念。随着马戏团的式微,新生代不再有机会观看到这样的演出,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,也很少有人走进一家剧院,花费几个小时安心地看一出表演。蒋雨希望能够通过绘画记录下这些消失的曾经,至少当人们停留在她画作前的几分钟的空隙里,可以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和温暖。
从“成长纪实”到“公园日记”系列,蒋雨的绘画与女儿一起成长。在成都出生、成长、工作,她的人生轨迹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。对艺术家来说,乐不思蜀是不存在的,乐而在蜀才是她真实的人生经历。这座城市闲散淡然的气质,深深地融合进她的骨血里。
有着众多公园的成都,既有如人民公园这样承载老成都悠闲生活方式的场所,又有像南郊公园这样绿意盎然、适合休闲漫步的天然氧吧,更有城市绿道等兼具生态与人文景观的现代公园。逛公园、泡茶馆,这是成都人打小就会做的两件事。从蒋雨外婆那一辈起,逛公园就是他们的日常。现在,当蒋雨的女儿与他们起争执后,也会自行到公园散心。
蒋雨的工作室附近有一片湿地保护区,每天午饭过后,她就会习惯性地到公园散步。当她因为创作较为沉重的“成长系列”感到心情烦闷时,只要在公园转个20分钟,压力便会显著减小,精神情况得到提升。
有些公园还在,有些公园只能停留在记忆当中。蒋雨爸爸工作厂区附近的八千家属院里的小公园,早已随着城市发展而消失,小时候看菊花展会的美好记忆却永远留在她的脑海中。那些发生在公园的一点一滴,被艺术家集结成“公园日记”系列。
小时候的蒋雨,生活的空白被大自然填满。公园仿佛有种魔力,时间在此停止了脚步。已是不惑之年的她再来到公园时,还是那些游船,还是那些陈设,好似一切都没改变。这一小片天地,将外面的喧嚣隔绝开来,只有岁月静好。


细心留意的话,会发现蒋雨作品里的鹅不是常见的天鹅,而是被蒋雨用自己的视角,戏剧化地处理过的家鹅。在她看来,天鹅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过遥远,人们更为熟悉作为家禽的鹅。以这种手法拉近画面的距离,带有艺术家的一些小“调皮”。“现在的孩子被太多学业缠身,不能走进剧院,起码家楼下的公园能带来一些安慰。”蒋雨发自内心地这么认为。
在“公园系列”中,虽然绘画的主题一致,但比起过往作品的“甜”,她增加了作品的粗粝感,并且融入了生命中的酸甜苦辣,不再似往常那般刻画纯粹的童话。这种变化,随着女儿进入青春期后带来的感受,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。
人生未必时刻尽如人意,在蒋雨看来,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物,有很多开心和感动的瞬间,以及让人们坚持和勇敢的理由。她希望自身的画作能在充满“褶皱”的生活中,打造出一个诗意的乌托邦,为世界带来“浮光”。同时,她希望提醒人们,不要忽视身边的风景。